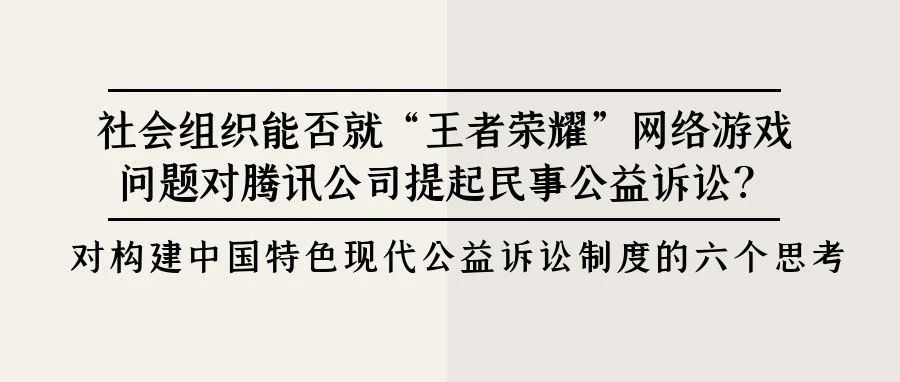中心原创
Webinar on the Revised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
Consider that the revision to the Law on the Protection … 阅读更多
未保法突破性规定与未检工作创新发展
文/佟丽华 来源:检察日报 10月17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… 阅读更多
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170项主要变化
文/于旭坤 2020年10月17日下午,全国人大三审通过了新修订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(以下简称“新未保法” … 阅读更多